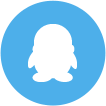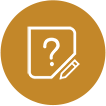清谈的兴起,大抵由于东汉末年党锢诸名士遭到政治暴力的摧残与压迫,一变其具体评议朝廷人物任用的当否,即所谓清议,而为抽象玄理的讨论。启自郭泰,成于阮籍。他们都是避祸远嫌,消极不与其时政治当局合作的人物。
东汉清议的要旨为人伦鉴识,即指实人物的品题。郭泰与之不同。《后汉书》列传五八《郭泰传》云:
"林宗《郭泰)虽善人伦,而不为危言靉论,故宦官擅政而不能伤也,及党事起,知名之士多被其害,惟林宗及汝南袁闳得免焉。"
又《世说新语,政事类》何骠骑作会稽条注引《郭泰别传》略云:
"泰宇林宗,有人伦鉴识。自著书一卷,论取士之本。未行,遭乱亡失。"
又《抱朴子,外篇》四六《正郭篇》云:
"林宗周旋清谈闾阁,无救于世道之陵迟。"
郭泰为党人之一,"有人伦鉴识",可是"不为危言駸论?而"周旋清谈闾阎"。即不具体评议中朝人物,而只是抽象研讨人伦鉴识的理论。故清谈之风实由郭泰启之。郭泰之所以被容于宦官,原因也在这里。
然而,郭泰是一个开端。魏晋两朝清谈又不是同一面貌,同一内容。魏晋清谈可分前后两期。魏末西晋时代为清谈的前期。此时期的清谈为当政洽上的实际问题,与其时士大夫的出处进退关系至为密切。换言之,此时期的清谈,是士大夫藉以表示本人态度及辩护自身立场的东西。东晋一朝为清谈后期。清谈至东晋只为口中或纸上的玄言,巳失去政治上的实际性质,仅止作为名士身份的装饰品。
前期清谈因为是与清谈者本人生活最有关的问题,即当日政治党系的表现,故值得研究。这有"四本论"和"竹林七贤"两个大问题。
《世说新语,文学类》云:"钟会撰《四本论》始毕,甚欲嵇公《嵇康)一见,置怀中,既定,畏其难,怀不敢出,于户外逋掷,便回急走。"
刘注云:
"《魏志》曰:会论才性同异,传于世。四本者,言才性同,才性异,才性合,才性离也。尚书傅蝦论同,中书令李丰论异,侍郎钟会论合,屯骑校尉王广论离。文多不载。"
《世说新语》此条刘注为前期清谈的重要资料。按第一篇《魏晋统治者之社会阶级》说过,曹操求才三令,大旨以为有德者未必有才,有才者或负不仁不孝贪诈的污名,即未必有德。性者,仁孝道德也。曹操求才三令讲的实际就是才性异、才性离的问题。三令为曹魏皇室大政方针之宣言,与之同者即是曹党,反之即是与曹氏为敌的党派。有关四本论的四个人,傅嘏、钟会论同与合,李丰、王广论异与离。就其党系而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