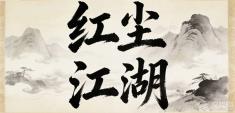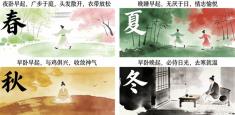试论“三王之道”——以“仲尼祖述尧舜”为切入点
作者:米继军
据《论语》中载:“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2]《论语集注》中曾对此注曰:“述,传旧而已;作,则创始也”;“孔子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皆传先王之旧而未尝有所作也。”[3]而《周易》中则亦载:“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此外,在《孟子字义疏证》及《日知录》中,则更分别征引孔子的话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4]。由此可见,孔子的思想与所谓“三王之道”之间,一定当存在着某些必然性的联系——并非什么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亦非他的什么天纵其智、突发奇想,而是其源有自、源远流长。
一、唐尧之道
有关于“唐尧之道”,在一部《尚书》之中,它是通过并借助于描画帝尧放勋个人丰功伟绩的形式来具体加以展现的:“聪明文思,光宅天下。将逊于位,让于虞舜……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5]这里之所谓“聪明文思”、“钦明文思”之“文思”或“文”,似可作先秦儒家之所谓“文质”之“文”解,亦即后来儒家之所谓“尊尊”;同时,“文思”又与“聪明”、“钦明”对举。也就是说,唯其“聪明”、“钦明”而“文思”而“尊尊”而制历、选贤、命官——大者如“将逊于位,让于虞舜”,这大概就是指这一时期的“禅让制度”。而所谓“禅让制度”本身,在本文看来,无疑即是其中最大的“尊尊”;而且其中,小者大概就是所谓“允恭克让”了。
如此的帝尧,自然是“聪明文思”、“钦明文思”的;而帝尧的如此,又必然会给当时整个社会带来“安安”、“庶绩咸熙”、“九族既睦”、“百姓昭明”、“黎民于变时雍”这一安定团结的良好社会政治局面,必然会给他本人带来“光宅天下”、“光被四表,格于上下”这一崇高而美好的声
在《中庸章句》里,朱熹曾对“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一句话作过这样一番精辟的解释:“祖述者,远宗其道;宪章者,近守其法。”——这里,前者云“远”而后者云“近”,前者曰“宗其道”而后者又曰“守其法”,真可谓深得机理、切中肯綮;与此同时,这里将“仲尼祖述尧舜”一句具体解作“远宗其道”,似乎亦不成问题。但为其所“宗”之“道”,在本文看来,却并非仅限于尧舜,而且似乎还应包括与此一脉相承的夏禹;换句话说,其所宗之道就是尧、舜、禹三王之道。而且在本文看来,这个道大概就是所谓“允执厥中”。因此与其说这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哲学方法或者哲学命题,不如说是一种明于人伦、关切政治的历史理念或者历史经验。据《史记?儒林列传》上说:“孔子闵王路废而邪道兴,于是论次《诗》、《书》,修起《礼》、《乐》。”这里的“《书》”,就是所谓《尚书》;而所谓的“论次”,若按照金景芳先生的解释:就是“去取上事”,“编排上事”[1]。既如此,则《尚书》中有关尧、舜、禹三王的“允执厥中”之道,也就成为以孔子、孟子等为代表的先秦儒家“中庸之道”的最早、也最直接的思想源头。
据《论语》中载:“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2]《论语集注》中曾对此注曰:“述,传旧而已;作,则创始也”;“孔子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皆传先王之旧而未尝有所作也。”[3]而《周易》中则亦载:“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此外,在《孟子字义疏证》及《日知录》中,则更分别征引孔子的话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4]。由此可见,孔子的思想与所谓“三王之道”之间,一定当存在着某些必然性的联系——并非什么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亦非他的什么天纵其智、突发奇想,而是其源有自、源远流长。
一、唐尧之道
有关于“唐尧之道”,在一部《尚书》之中,它是通过并借助于描画帝尧放勋个人丰功伟绩的形式来具体加以展现的:“聪明文思,光宅天下。将逊于位,让于虞舜……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5]这里之所谓“聪明文思”、“钦明文思”之“文思”或“文”,似可作先秦儒家之所谓“文质”之“文”解,亦即后来儒家之所谓“尊尊”;同时,“文思”又与“聪明”、“钦明”对举。也就是说,唯其“聪明”、“钦明”而“文思”而“尊尊”而制历、选贤、命官——大者如“将逊于位,让于虞舜”,这大概就是指这一时期的“禅让制度”。而所谓“禅让制度”本身,在本文看来,无疑即是其中最大的“尊尊”;而且其中,小者大概就是所谓“允恭克让”了。
如此的帝尧,自然是“聪明文思”、“钦明文思”的;而帝尧的如此,又必然会给当时整个社会带来“安安”、“庶绩咸熙”、“九族既睦”、“百姓昭明”、“黎民于变时雍”这一安定团结的良好社会政治局面,必然会给他本人带来“光宅天下”、“光被四表,格于上下”这一崇高而美好的声
点击展开查看全文
展开全文
APP阅读
特色专题
更多精彩推荐
国学指南
更多 >热门栏目
更多 >热门文章
更多 >
元代的“四等人制”是不是一个历史误解?
国学杂谈
丁忧制度下,官员怎样在忠孝之间寻找平衡点?
国学杂谈
从“狗国”到“水土”,晏子如何用节奏与隐喻,在羞辱中反客为主?
国学杂谈
“吃醋”形容嫉妒,真的源于唐太宗那杯恶作剧的“毒酒”吗?
国学杂谈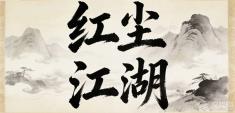
为什么“江湖”不再指江水,“红尘”不单是飞尘?一场词义的文化迁徙
国学杂谈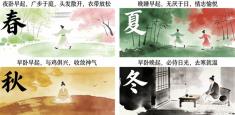
我们能否既拥抱现代生活,又不辜负身体的四季之歌?
国学杂谈
屋檐下的“豕”:一个“家”字,为何能牵出整个远古文明史?
国学杂谈
为什么说“近朱者赤”是现代人摆脱孤独的良方?
国学杂谈
如果大观园实行“贡献点制度”,宝玉还能当他的“闲人”吗?
国学杂谈
茶道如何帮助我们学会“拿起与放下”?
国学杂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