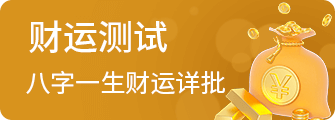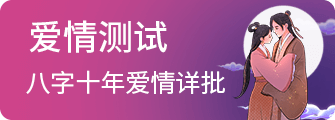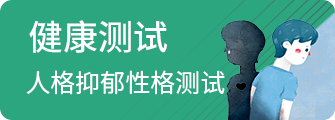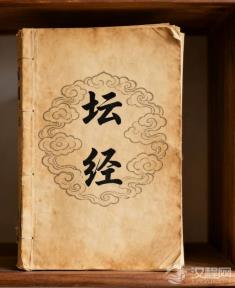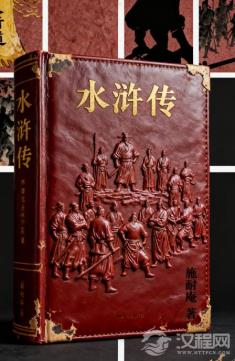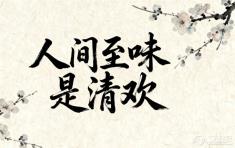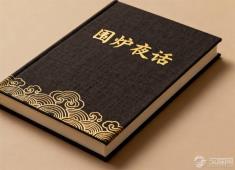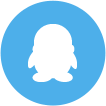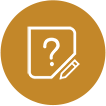道的可知性
作者:王受仁
关于道的可知性,我们还可从以下几节章句来证实:
如第十四章,这一章是老子描写道的虚无状态,如看不见,听不着,摸不到,“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恍恍惚惚的东西。但是,老子最后说:“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谓道纪。”这就是讲,尽管道是如此的玄妙,但是,只要我们能够掌握住古代的大道,我们就能驾驭今日存在的现实。只要我们能够知道远古原始的开始,我们就能知道道的规律。这是老子对道的可知性,从一个侧面的表述。
如第二十一章,这一章是老子描写道的实有状态的,如“道之为物,惟恍惟惚”,“其中有象”,“其中有物”等等的描写。老子在最后评价其道说:“自今及古,其名不去,以阅众甫。吾何以知众甫之状哉?以此。”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这个自古至今,亘古未变的道,我们就是凭着对它的了解,才使我们认识到万物的本源,认识到万物的各种状态。这是老子对道的可知性,从另一个侧面的表述。
如第十五章,这一章是对古代知“道”或“善为道者”士的一段生动形象的描述,从有具体人的知“道”和“善为道者”的角度的存在,也可说明老子认为道是完全可以知的。
另外,在老子的5000言中,压根就没有讲过一句类似这样的话,道是不可知的。
二、老子知“道”的特有方法
在老子五千言中,我总结老子知“道”的方法有两个:其一是直观体察原则;其二是简约抽象原则。
其一,直观体察原则。
老子在四十七章中讲了自己与众不同的学道方法,即:“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一大段话,老子这一段话与我们今天所学到的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认识观是相悖的,对于这样一个问题,我认为必须从历史的观点来看待老子认识论。在当时古代生产力极度低的条件下,要认识一个如此高深莫测的大理论问题,强调实践出真知是很不切实际的,因此,在知“道”过程中理论的思维必然要突显出来。而理论的思维又必须有经验可靠的材料为对象,所以在当时
老子所认定的自然之道可不可以认识呢?从五千言文章的整体来看,可以肯定地说,老子认为道是可知的,尽管老子对道的描述用了“玄”字,“玄之又玄,众妙之门”(1章),还用了“奥”字,“道者,万物之奥”(62章),又用了“隐”字,“道隐无名”(41章)等等,因而给人感觉“道”好似是玄乎不可察;隐藏很深不可测;道理深奥不可知的东西。其实,老子的本意完全不是这样的,老子这样讲,无非是想说明道的存在的内在性,理性的深奥性。而道的存在和它的理性,并非不可知,而是完全可察、可测和可知的。
关于道的可知性,下面拟从四个方面阐述:一、知“道”的可知性;二、老子知“道”特有的方法;三、老子认为有碍知“道”的阻力;四、最后我的反思。
一、知“道”的可知性
老子在第一章开门见山就说了:“道可道,非常道”。“道可道”就是说道是可以知,可以说的。虽然这里讲的可知可说的道是“非常道”,但老子在以后的章句中并没有说“常道”就不可以知的,相反说了常道也是可以知的,如“知常曰明”(16章),“知和曰常,知常曰明”(55章),“明白四达,能无知乎”(10章),“使我介然有知,行于大道”(53章)等等,所有这些,老子都是十分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道是可以知的。所以我非常同意孙以楷先生在《老子通论》中的一句概括:“五千言中的主要内容是论述道、知道、治道”。因此道的可知性在老子论道中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
关于道的可知性,我们还可从以下几节章句来证实:
如第十四章,这一章是老子描写道的虚无状态,如看不见,听不着,摸不到,“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恍恍惚惚的东西。但是,老子最后说:“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谓道纪。”这就是讲,尽管道是如此的玄妙,但是,只要我们能够掌握住古代的大道,我们就能驾驭今日存在的现实。只要我们能够知道远古原始的开始,我们就能知道道的规律。这是老子对道的可知性,从一个侧面的表述。
如第二十一章,这一章是老子描写道的实有状态的,如“道之为物,惟恍惟惚”,“其中有象”,“其中有物”等等的描写。老子在最后评价其道说:“自今及古,其名不去,以阅众甫。吾何以知众甫之状哉?以此。”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这个自古至今,亘古未变的道,我们就是凭着对它的了解,才使我们认识到万物的本源,认识到万物的各种状态。这是老子对道的可知性,从另一个侧面的表述。
如第十五章,这一章是对古代知“道”或“善为道者”士的一段生动形象的描述,从有具体人的知“道”和“善为道者”的角度的存在,也可说明老子认为道是完全可以知的。
另外,在老子的5000言中,压根就没有讲过一句类似这样的话,道是不可知的。
二、老子知“道”的特有方法
在老子五千言中,我总结老子知“道”的方法有两个:其一是直观体察原则;其二是简约抽象原则。
其一,直观体察原则。
老子在四十七章中讲了自己与众不同的学道方法,即:“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一大段话,老子这一段话与我们今天所学到的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认识观是相悖的,对于这样一个问题,我认为必须从历史的观点来看待老子认识论。在当时古代生产力极度低的条件下,要认识一个如此高深莫测的大理论问题,强调实践出真知是很不切实际的,因此,在知“道”过程中理论的思维必然要突显出来。而理论的思维又必须有经验可靠的材料为对象,所以在当时
点击展开查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