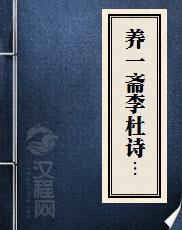简介
知识导读
更多 >- 暂无数据,敬请期待!
留言讨论


养一斋诗话
“诗言志”,“思无邪”,诗之能事毕矣。人人知之而不肯述之者,惧人笑其迂而不便於己之私也。虽然,汉、魏、六朝、唐、宋、元、明之诗,物之不齐也。“言志”、“无邪”之旨,权度也。权度立,而物之轻重长短不得遁矣;“言志”、“无邪”之旨立,而诗之美恶不得遁矣。不肯述者私心,不得遁者定理,夫诗亦简而易明者矣。言志者必自得,无邪者不为人。是故古人之诗,本之於性天,养之以经藉,内无怵迫苟且之心,外无夸张浅露之状;天地之间,风日月,人情物态,无往非吾诗之所自出,与之贯输於无穷。此即深造自得,居安资深,左右逢原之说也,不为人故也。後世之士,若不为人,则不复学诗;搦管之先,求胜人,多作之後,遂思传世,虽久而成集,阅之几无一言之可存。何也?彼原未尝学诗也。分曹咏物之作,酬和叠韵之体,谀颂悦人之篇,考古之制,穷工极巧,イ漫浩汗,何益於身心,何裨於政教?作者诩能手,诵者称国工,名家不能扫除,馀子倚为活计,纷纷籍籍,皆孔子所谓为人者也。此乌得有自得之一时,使人一唱三叹讽寻不置哉!难者曰:“为己自得,圣学也,学诗必要诸圣,不迂则僭。”曰:“子知诗宜辨雅俗乎?”曰:“知之。”曰:“知之则无疑予言之迂且僭也。夫所谓雅者,非第词之雅驯而已;其作此诗之由,必脱弃势利,而後谓之雅也。今种种斗靡骋妍之诗,皆趋势弋利之心所流露也。词纵雅而心不雅矣,心不雅则词亦不能掩矣。不雅由於为人而不自得,然则子欲画雅俗之界,舍为己自得之说,又何从辨之?《三百篇》、汉人之诗,委巷妇孺,亦厕其中,彼岂尝探讨圣学者,特其诗不为人而自得,故足传诵耳。子於此求之,则知予非好作头巾语矣。不审乎此,而震惊时俗之同然,依傍他人之门户,无志无识,终於苟焉耳。何诗之可言!”仕而不知为人,学而不知为己,本是通病,何责於诗?即以诗论,此病亦不起於一时。西晋以降,陆机、谢灵运、颜延年辈为已斗靡骋妍,求悦人而无真气。一千五百年来,相沿相袭,虽有超世复古之士,不能尽涤悦人之念,则亦不能尽洗斗靡骋妍之诗,而又何慨焉!虽然,传之愈久,则正之愈难,正之愈难,则挽回之心愈不可已。此吾所以不量其力,发愤抒词,甘受人之笑骂而不顾也。阿谀诽谤,戏谑淫荡,夸诈邪诞之诗作而诗教熄,故理语不必入诗中,诗境不可出理外。谓“诗有别趣,非关理也”,此禅宗之馀唾,非风雅之正传。《三百篇》之体制音节,不必学,不能学;《三百篇》之神理意境,不可不学也。神理竟境者何?有关系寄托,一也;直抒己见,二也;纯任天机,三也;言有尽而意无穷,四也。不学《三百篇》,则虽赫然成家,要之纤琐摹拟,浅尽而已。今人之所喜,古人之所笑也。汉、唐人不尽学《三百篇》,然其至高之作,必与《三百篇》之神理意境ウ合,而後可以感人而传诵至今。夫才高者,尚可ウ合,而何不可学之有哉!东坡先生教人作诗曰:“熟读《毛诗国风》与《离骚》,曲折尽在是矣。”王伯厚曰:“《新安吏》:‘仆射如父兄。’‘虽则如毁,父母孔迩’,此诗近之。山谷所谓‘论诗未觉《国风》远’也。”王济之曰:“读《诗》至《绿衣》、《燕燕》、《硕人》、《黍离》等篇,有言外无穷之感。唐人诗尚有此意,如‘君向萧湘我向秦’,不言怅别而怅别之意溢於言外;‘潮打空城寂莫回’,不言兴亡而兴亡之感溢於言外,最得风人之旨。”愚谓此类甚多,皆《三百篇》可学之证也。後世诗学之卑,或由见诗太少,或由见诗太多。少见不足论,多见亦是病痛者,盖宋、元以後,流布之集,插架累累,半属浮花浪蕊,而士之学诗以争名者,尤必多取时世能手之诗,勤勤观法,故诗名愈速而诗格乃愈卑。宋人诗曰:“男儿无英标,焉用读书博!”书之博,无救於品之庸,况博读时人之诗哉!亦相率为庸而已矣。人与诗有宜分别观者,人品小小缪戾,诗固不妨节取耳。若其人犯天下之大恶,则并其诗不得而恕之。故以诗而论,则阮籍之《咏怀》,未离於古;陈子昂之《感遇》,且居然能复古也。以人而论,则籍之党司马昭而作《劝晋王笺》,子昂之谄武而上书请立武氏九庙,皆小人也。既为小人之诗,则皆宜斥之为不足道,而後世犹赞之诵之者,不以人废言也。夫不以人废言者,谓操治世之权,广听言之路,非谓学其言语也。籍与子昂诚工於言语者,学之则亦过矣!况吾尝取籍《咏怀八十二首》、子昂《感遇三十八首》反覆求之,终归於黄、老无为而已。其言廓而无稽,其意奥而不明,盖本非中正之旨,故不能自达也。论其诗之体,则高拔於俗流,论其诗之义,则浸淫於隐怪,听其存亡於天地之间可矣。赞之诵之,毋乃崇奉忄佥人而奖饰讠皮辞乎!宋人论诗,每以陶、阮并称。不知陶之天机自运,其言平易而昭明,君子之诗也;阮之荒唐隐谲,纯为避祸起见,小人之诗也。尚不逮嵇中散之朴直,何论陶彭泽哉!元人云“论功若准平吴例,合著黄金铸子昂”者,亦误也。唐之复古者,始於张曲江,大於李太白,子昂与曲江先後不远。子昂《
潘德舆清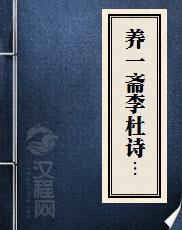
养一斋李杜诗话
养一斋李杜诗话清潘德舆●卷一朱子曰:“作诗先看李、杜,如士人治本经,本既立,方可看苏、黄以次诸家。”予笃信此说,十年前,辑《作诗本经》一书,专取李、杜集,择而录之,并为《总论》二卷附焉。既而思之,李、杜所作,诚不能篇篇与《风》、《雅》合,然非浅陋如予者所宜定去取也,故此书不敢示人。其《总论》则偶出管见,不忍割弃,缀诸拙著诗话後,质世之知言者。朱子曰:“李太白诗非无法度,乃从容於法度之中,盖圣於诗者。”按古今论太白诗者众矣,以朱子此论为极则。他人形容赞美,累千百言,皆非太白真相知者,以本不知诗教源流。故子美为“诗圣”,而太白则谓之“诗仙”,万口熟诵,牢不可破。究竟仙是何物?以虚无不可知者相拟,名尊之实外之矣。若缘谪仙之号定於贺监,谪仙之歌赋於同朝,少陵赠什亦尝及之,遂为定评。不知贺监老为道士,回惑已深,明皇好仙,朝列风靡,无稽品藻,何足效尤;少陵特叙其得名之始云尔,非以为确不可易也。且贺监又尝目之为天上星精矣,岂亦可从张旭太湖精之例,以“诗精”目之乎?若见太白咏仙者多,乃以“诗仙”当之,则高如郭璞,卑若曹唐,亦将号以“诗仙”耶?朱子以其徒容法度为圣,何等了当!杨升庵曰:“太白为古今诗圣。”语据朱子,扌颠扑不破。而他日又谓“太白诗仙翁剑客语”,何其仙圣之杂糅也!此义不明,看太白诗焉能入解?故皮袭美谓其诗“言出天地外,思出鬼神表,非世间人语”。极力推尊,皆成幻妄。歼氏臞庵谓其诗“如刘安鸡犬,遗响白云,覈其归存,恍无定处”。推寻不入,转致揶揄也。至王氏百谷,乃直谓“李诗仙,杜诗圣,圣可学,仙不可学矣”。岂非名尊之、实外之之明验也哉!惟周氏伯弓曰:“太白诗号雄俊,而法度最缜密。”此乃可与朱子之言相发明耳。张氏邦基曰:“孟子之言道,如项羽用兵,直行曲施,逆见错出,皆当大败,而举世莫能当,何其横也!左丘明之於词令亦甚横。自汉後千年,惟韩退之之於文,李太白之於诗,亦皆横者。”按孟子不可以“横”言,左氏亦不可以“横”尽。若“项羽之用兵,直行曲施,逆见错出,举世莫能当”,拟太白诗,颇得其神。然朱子云:“太白诗不专是豪横,亦有雍容和缓者,如首篇‘《大雅》久不作’,多少和缓?”此论又不可不知也。计氏有功曰:“张碧,贞元中人,自序其诗云:‘尝读李长吉集,谓春拆红翠,辟开蛰户,其奇峭不可攻也。及览太白诗,天与俱高,青且无际,鹍触巨海,澜涛怒翻,则观长吉之篇,若陟嵩之颠视诸阜者耶!’”按《沧浪诗话》云:“人言太白仙才,长吉鬼才,不然,太白天仙之词,长吉鬼仙之词耳。”《海录碎事》亦言:“唐人以李白为天才绝,白居易人才绝,李贺鬼才绝。”又渔洋山人戏论“李白飞仙语,李贺才鬼语”。愚实不解仙鬼之才、仙鬼之语,诸公何从悉其高下而公然以评诗也?张碧论太白,长吉别处,奇古确实,远胜天仙、鬼仙、鬼才、才鬼诸说。碧诗万不可以追踪太白,而名碧字太碧,摹仿令人失笑,然此论独可存也。严氏羽曰:“观太白诗者,要识真太白处。太白天才豪逸,语多卒然而成。学者於每篇中,识其安身立命处可也。”按沧浪论诗,以禅为喻,颇非古义,所以来冯氏之攻。然谓“李、杜二集,须枕藉观之,如今人之治经”,则吻合朱子之谕,不可攻也。其谓太白诗有“安身立命处”,语殊深微不易解,而於太白诗煞有见地,学者不可不究其旨。究之若何?吴子华所谓“太白诗气骨高举,不失颂咏风刺之遗”者,即其“安身立命处”矣。沧浪又谓“太白发句,谓之开门见山”。夫诗有通体贵含蓄者,有通体贵发露者,岂有“发句”必求“开门见山”之理?此可以论唐人试帖之破题,而不可以论太白诗也。误传惑人,莫此为甚,故附辩之。魏氏庆之曰:“为诗欲气格豪逸,当看退之、太白。”按退之文,乃太白诗之敌也;退之诗,则不可与太白诗并。盖退之诗,豪则有之,逸处甚少,千古以来,足当“气格豪逸”者,太白一人而已。後来苏长公七古豪逸处,几欲乱真。然李诗源出《风》、《骚》,痕迹都融;苏诗行以古文,议论不废。李实正声,苏为别径,终难方驾。朱子曰:“苏、黄只是今人诗,苏才豪,一滚说尽无馀意。”是也。杨氏慎曰:“庄周、李白,神於文者也,非工於文者所及也。文非至工,则不可为神,然神非工之所可至也。”按升庵轩李轾杜,不足训,此以庄子比太白,却不误。顾氏璘亦云:“文至庄,诗至太白,草书至怀素,皆兵法所谓奇也。”然怀素之草书,非右军之左规右矩也;太白却於古法无脱漏处耳。黄氏庭坚曰:“太白歌诗,超越六代,与汉、魏乐府争衡。”按《李诗纬》云:“太白愠于群小,乃放还山,纵酒浪游,岂得已哉!故於乐府多清怨,盖不敢忘君也。”夫太白之不敢忘君,与子美何
潘德舆清
示儿长语
示儿长语清·潘德舆○心法吟为禽为兽,为孝为忠。天壤悬隔,方寸之中。尔心能存,目明耳聪。尔心不存,目瞽耳聋。尔心能存,荣及祖宗。尔心不存,灾及尔躬。何穷何通,何吉何凶,正心淫心,天不梦梦。毋黠而惰,宁拙而恭。宁直而啬,毋曲而丰。五经之外,更无信从。五伦之外,更无事功。五常之外,更无心胸。士不治心,不如力农。○作人诗七章作人先立志,志立乃根基。人无向上志,念念入涂泥。从善天所命,尔毋迷途歧。念念循善念,大端为顺亲。何不从亲训,而乃从他人?悖德者自思,何以有此身?顺亲非面貌,反身诚为主。外顺内悖之,禽兽衣冠伍。魂梦内省来,欺诈速宜去。诚心顺亲者,作事必识羞。惟恐辱吾亲,戏荡是吾仇。匪人引货色,断不与交游。识羞知正路,步步学谨慎。守身如执玉,保德保性命。一言不敢妄,矧敢有恶行?谨慎自勤业,读书真读书。熟读复细思,无处肯模糊。将求古人心,立品与之俱。凡吾之所言,经传咸已具。古训谁不闻?嗜欲绊乃误。斩欲始作人,失足悔迟暮。右诗七章,章章相衔接而下,以首章为提纲,以末章为归宿。中五章□顺亲,仁也;诚身,信也;识羞,义也;谨慎,礼也;读书,智也。五常具备,万事万物之理,不出乎此矣。所以不言五常之名目,不依其自然之次序者,以言其理,则名目可不言也。且五常之理,甚大而精,姑言浅近急切之端,以自成其次序耳。顺亲、诚身,虽非浅近,而小子肯听父母教训,亦为顺亲;肯踏实作事,绝不说谎欺人,亦为诚身,此皆最急之事。识羞、谨慎,皆踏实做工夫处,故即次之。读书,在作人为余事,乃智之一端,故置之后;然非此不能明理以诚其身,故足与上四者相配而立也。总之,先非立志,则善无原;终非斩欲,则恶不净。故首、末二章,尤吃紧也。能率首、末二章之意,而中五章,乃一线穿成矣。以“作人”二字命题,明从此,则为人;不从此,则为禽兽也。欲为人乎?欲为禽兽乎?如之何勿思?孟子曰:“我固有之也,弗思尔矣。”“岂爱身不若桐梓哉?弗思甚也。”“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人人有贵于己者,弗思耳。”故“思”字最要。思之熟乃能立志耳。程子亦曰:为恶之人,未尝知有思;有思,则为善矣。一心为善,非立志而何。知羞能吃苦,踏实自生明(肯吃苦而不寻乐,必是个出色男子)。理义为真我,《诗》、《书》是后天。聪明而浮游,非有成之材也。鲁钝之质而又有浮游之心,吾不知之矣。“孝弟忠信,礼义廉耻”八字,尔辈知其当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故视若束缚人之物而苦之也。知其所以当然之故,则不苦之矣。此非思不可也。口讲耳闻,皆当然者也;学也,学而不思则罔,罔则苦也。讲日记故事,孝子悌弟,便有思齐之心,方是有才情后生。肯读书者,远到不信道,为下愚。只要一个真心,“真心”者,耻也。先求专诚不欺,再讲余事。天下无一事能假,天下无一人可欺。不能假而假之,其徒假也──可笑。不能欺而欺之,其自欺也──可哀。浑朴如孺子,微细如鸟雀,而不能欺之言色间,况进于此者乎?孝弟者,人之元气;廉耻者,人之骨干;忠信者,人之心肝,试思此,有一时可无者乎?经、史,饮食也,所谓“后天”也,亦不可废也。○读书三要字句清朗,遍数满足,常常自背。读书二大要思之,行之。○读书五则凡读书,须为终身计。古人每日只读一本书,一本书只读二、三百字,二、三百字便读二、三百遍,所以终身不再读此书,而无不熟也。所以有余力读他书、生书,无一日停,而能无书不读也。尔辈始而生书,继而熟书,终而带背,似手法详虑密。究竟读生书时,预备做熟书,再加遍;读熟书时,预备归带背时,再加遍。挨次姑待,无一踏实透熟之时,故已
潘德舆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