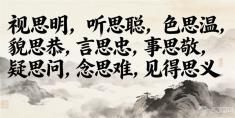《文心雕龙·隐秀篇》主旨新说
作者:陶水平
【内容提要】
刘勰《文心雕龙》卷四十为《隐秀》篇。由于上篇原文不全,关于《隐秀》篇的主旨或“隐秀”的涵义,历来众说纷纭。本文在辩析刘勰原著与总结近年各种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认为《隐秀》篇的主旨是从创作论的角度谈言意关系,或从修辞论的角度来探讨文学创作的规律。“隐秀”问题与“比兴”问题有最密切的联系。“隐秀”论的提出,也是刘勰针对文学发展的历史与现状的有感之发。作为对我国古代文学作品的一条重要的内在规律的揭示,刘勰的“隐秀”论与他同时代的钟峰的“滋味”论一样,成为中国古代文学意境论形成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关键词】隐秀/创作论/修辞论/作品论/比兴/六朝文学
一
《文心雕龙》卷四十有《隐秀》专篇,在全书的理论结构中属“剖情析采”的重要部分。但对于本篇部分的文字的真伪问题,几百年来一直存在争议。从现存《文心雕龙》的最早刻本元至历十五年刻本到明历三十七年以前的各种刊本,本篇都缺四百余字。直至明末,钱功甫据所见宋本钞补了从“澜表方圆”以下至“朔风动秋草”的“朔”字之前的四百多字。清人纪昀批《文心雕龙》时,断定《隐称》篇补文系明人伪作,纪氏并把他的考证意见著录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九十五《文心雕龙》的《提要》中。此后,这一判断长期为人们普遍接受,如近人黄侃,今人范文澜、刘永济、杨明照、王达津等[1],均同意纪说,并称这四百字的补问乃明人伪造。但是,时至本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詹yīng@①先生两度撰文,广参博考,力证其真[2]。周汝昌先生也接着著文,经多方考辩,认定这四百字的补文大体上系彦和原文,其言材料凿凿,论证有力[3]。当然,还有一些德高望重、造诣极深的“龙学”专家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一种意味深长的沉默。总之,《隐秀》补文的真伪问题迄今仍是一个学术公案,如无实物佐证,一时恐难成为定论。由此也给《隐秀》篇的理论研究留下了遗憾,增加了难度。关于《隐秀》篇主旨的探讨,自然也就出现了许多意见,真是见仁见智,莫衷一是。《隐秀》篇与几乎《原道》《风骨》等篇一样,成了《文心雕龙》一书中争议最多最大的篇目之一。
关于《文心雕龙·隐秀篇》的主旨,学术界主要有以下几种意见:
1.风格论:
【内容提要】
刘勰《文心雕龙》卷四十为《隐秀》篇。由于上篇原文不全,关于《隐秀》篇的主旨或“隐秀”的涵义,历来众说纷纭。本文在辩析刘勰原著与总结近年各种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认为《隐秀》篇的主旨是从创作论的角度谈言意关系,或从修辞论的角度来探讨文学创作的规律。“隐秀”问题与“比兴”问题有最密切的联系。“隐秀”论的提出,也是刘勰针对文学发展的历史与现状的有感之发。作为对我国古代文学作品的一条重要的内在规律的揭示,刘勰的“隐秀”论与他同时代的钟峰的“滋味”论一样,成为中国古代文学意境论形成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关键词】隐秀/创作论/修辞论/作品论/比兴/六朝文学
一
《文心雕龙》卷四十有《隐秀》专篇,在全书的理论结构中属“剖情析采”的重要部分。但对于本篇部分的文字的真伪问题,几百年来一直存在争议。从现存《文心雕龙》的最早刻本元至历十五年刻本到明历三十七年以前的各种刊本,本篇都缺四百余字。直至明末,钱功甫据所见宋本钞补了从“澜表方圆”以下至“朔风动秋草”的“朔”字之前的四百多字。清人纪昀批《文心雕龙》时,断定《隐称》篇补文系明人伪作,纪氏并把他的考证意见著录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九十五《文心雕龙》的《提要》中。此后,这一判断长期为人们普遍接受,如近人黄侃,今人范文澜、刘永济、杨明照、王达津等[1],均同意纪说,并称这四百字的补问乃明人伪造。但是,时至本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詹yīng@①先生两度撰文,广参博考,力证其真[2]。周汝昌先生也接着著文,经多方考辩,认定这四百字的补文大体上系彦和原文,其言材料凿凿,论证有力[3]。当然,还有一些德高望重、造诣极深的“龙学”专家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一种意味深长的沉默。总之,《隐秀》补文的真伪问题迄今仍是一个学术公案,如无实物佐证,一时恐难成为定论。由此也给《隐秀》篇的理论研究留下了遗憾,增加了难度。关于《隐秀》篇主旨的探讨,自然也就出现了许多意见,真是见仁见智,莫衷一是。《隐秀》篇与几乎《原道》《风骨》等篇一样,成了《文心雕龙》一书中争议最多最大的篇目之一。
关于《文心雕龙·隐秀篇》的主旨,学术界主要有以下几种意见:
1.风格论:
点击展开查看全文
展开全文
APP阅读
特色专题
更多精彩推荐
国学指南
更多 >热门栏目
更多 >热门文章
更多 >
当代人焦虑内耗,是不是丢了国学里的幸福智慧?
国学文化
西游师徒四人的不完美,藏着怎样的成长真相?
国学文化
古人的 “抗挫力” 从何而来?国学智慧给出了怎样的答案?
国学文化
为什么说分寸感是成年人最稀缺的高级情商?
国学文化
董仲舒的“交易”:用“独尊儒术”为儒家换来千年尊荣,是福是祸?
国学文化
《诗经》爱情课:在礼教与自由之间,古人如何勇敢说爱?
国学文化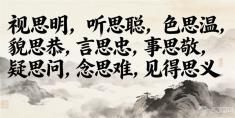
《论语》里的“君子九思”,如何让现代人脱胎换骨?
国学文化
“知行合一”太高深?如何从“知道却做不到”的怪圈起步?
国学文化
《道德经》里这3个字,专治当代人的“想太多”
国学文化
如果说童年安装的“软件”影响一生,那么我们该为下一代选择怎样的“启蒙程序”?
国学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