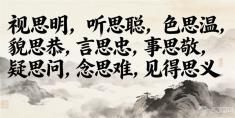楚簡《恆先》“祥義利巧綵物出於作”解
作者:曹 峰
《恆先》第七號簡有“恙宜利主,采勿出於作”這樣一句話。董珊先生《楚簡〈恆先〉詳宜利巧解釋》[1]一文,從古文字學的角度,論證了原作“主”的字應當讀爲“丂(巧)”,因此“利主”就是“利巧”。筆者認爲這個解釋是非常有説服力的,因爲不僅文字學上的考證令人信服,而且如董珊先生所指出的那樣,郭店楚簡《老子》甲本第一號簡有“絶巧棄利,盗賊無有”(王弼本第十九章相同),可見,“巧”和“利”是意義相近,可以并用的詞匯。筆者在《〈恆先〉編聯、分章、釋讀札記》[2]一文中,曾從龐樸先生《〈恆先〉試讀》[3],將該處文句讀爲“詳義利,主綵物、出於作”。但後來經過考證,確認“恙宜”就是“祥義”,所以,將這句話三字一讀是不合適的。於是想到“恙宜利主”既然與“采勿出於作”對文,“恙宜利主”的中間也許脱寫一“於”字,原文可能是“恙宜利[於]主,采勿出於作”。[4]看到董珊論文之後,我決定放棄自己的主張。董珊先生把“利主”釋爲“利巧”,使《恆先》的這處難關終於突破了。
然而,在這句話的解釋上,筆者的想法卻完全不同,在此想與董珊先生商榷。不同之處在於以下三個方面。第一,“恙宜”究竟應該如何解釋?第二,“巧”是否指的是導致“名實”關係走向不確定的語言上的“巧詐”?第三,“恙宜利巧”四字與上下文的關係究竟如何?
首先來歸納一下《楚簡〈恆先
《恆先》第七號簡有“恙宜利主,采勿出於作”這樣一句話。董珊先生《楚簡〈恆先〉詳宜利巧解釋》[1]一文,從古文字學的角度,論證了原作“主”的字應當讀爲“丂(巧)”,因此“利主”就是“利巧”。筆者認爲這個解釋是非常有説服力的,因爲不僅文字學上的考證令人信服,而且如董珊先生所指出的那樣,郭店楚簡《老子》甲本第一號簡有“絶巧棄利,盗賊無有”(王弼本第十九章相同),可見,“巧”和“利”是意義相近,可以并用的詞匯。筆者在《〈恆先〉編聯、分章、釋讀札記》[2]一文中,曾從龐樸先生《〈恆先〉試讀》[3],將該處文句讀爲“詳義利,主綵物、出於作”。但後來經過考證,確認“恙宜”就是“祥義”,所以,將這句話三字一讀是不合適的。於是想到“恙宜利主”既然與“采勿出於作”對文,“恙宜利主”的中間也許脱寫一“於”字,原文可能是“恙宜利[於]主,采勿出於作”。[4]看到董珊論文之後,我決定放棄自己的主張。董珊先生把“利主”釋爲“利巧”,使《恆先》的這處難關終於突破了。
然而,在這句話的解釋上,筆者的想法卻完全不同,在此想與董珊先生商榷。不同之處在於以下三個方面。第一,“恙宜”究竟應該如何解釋?第二,“巧”是否指的是導致“名實”關係走向不確定的語言上的“巧詐”?第三,“恙宜利巧”四字與上下文的關係究竟如何?
首先來歸納一下《楚簡〈恆先
点击展开查看全文
展开全文
APP阅读
特色专题
更多精彩推荐
国学指南
更多 >热门栏目
更多 >热门文章
更多 >
为什么说分寸感是成年人最稀缺的高级情商?
国学文化
董仲舒的“交易”:用“独尊儒术”为儒家换来千年尊荣,是福是祸?
国学文化
《诗经》爱情课:在礼教与自由之间,古人如何勇敢说爱?
国学文化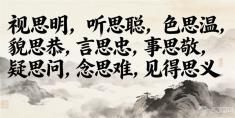
《论语》里的“君子九思”,如何让现代人脱胎换骨?
国学文化
“知行合一”太高深?如何从“知道却做不到”的怪圈起步?
国学文化
《道德经》里这3个字,专治当代人的“想太多”
国学文化
如果说童年安装的“软件”影响一生,那么我们该为下一代选择怎样的“启蒙程序”?
国学文化
在教养中“做减法”:如何用道家智慧养出内心强大的孩子?
国学文化
筷子起落间的修养:《礼记》教会我们什么?
国学文化
“家训”文化:《颜氏家训》与《朱子家训》的当代启示
国学文化